第一卷 波罗蜜(第13/22页)
装铁窗铁门也就罢了,几乎没有人愿意在上面花一点心思。我常常在想,铁窗虽然是单调乏味的东西,如果有很好的设计,可以使它变成很现代的花坛,或者甚至不觉得它是铁窗。铁卷门也是如此,镂空雕花之后感觉就会完全不同,或者把它当成画布,提供给艺术家创作,或者让小学的学生来作儿童画,那么,在入夜以后和清晨之前,整个城市都会有鲜丽的色彩和无所不在的美术教育了。
工地,也是台北的奇景。大楼鹰架上一放就是几年的看板,捷运工程围堵了整条道路的铁板,这都是城市最好的画布,但是从来没有人去正视或处理它。一整个城市到处都变得非常丑怪、单调、机械,没有一点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天桥也是的,在我居住的地方就有几条架在马路上空的天桥,它们没有一丝颜色,也未曾有过设计,它就灰蒙蒙的搁在那里,呆滞、没有美感。地下道和天桥是同样的东西,它的灰黯、冷寂,没有色彩,也一如天桥。
其实,在我看来,台北到处都是画布,都是文化美感建立的起点,问题只在于我们根本不想美化这个城市,就像懒于在自家商店的铁卷门花心思一样。
我们的美感教育逐渐在背离生活,成为一种荒诞空洞的东西。我就知道有的企业家花上数百万美元在国外标购艺术品,可是他自己的办公室连一幅画、一个盆栽、一束鲜花都没有。有的富人花上数十万元买一个田黄或鸡血印章面不改色,可是走到百货公司,却没有眼光挑出一个具有美感的茶杯。开百万名车出街的阔佬,很多人家里还挂着外销画和美女月历。
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台北流行茶艺馆,这些消费奇高的茶艺馆都十分讲究装潢,动辄千百万,尽一切可能把它做得像从前乡下的茅房,茅草盖顶、旧的竹帘、粗俗的桌椅,再挂上几盏昏黄的风灯,认为这样是乡土风味或中国风味,我每次走进这种地方就仿佛闻到了当年茅房的气味。
在台北喝茶是世界最贵的。喝咖啡也是世界最贵的。我去过几家一杯咖啡两三百元的店里,也是以装潢取胜,但墙上挂的是拙劣的古典主义仿作,桌椅则是欧洲著名设计师的仿冒品,拿这样的装潢,来卖一杯咖啡三百元,不知道理何在?
而在忠孝东路上,不管是大百货公司、大饭店,或是小的服饰店、咖啡屋,似乎都流行装潢,每隔一两年都要大肆装潢一番,这样的事可以从两个观点看,一是经营者和设计者的眼光短浅,二是没有人想要经营一家有品味的老店。于是整条街都是浮浅、骚动的,随时都在变化、装潢,缺乏大城大道(像巴黎的香榭里、纽约的曼哈顿、东京的银座)那种宁静庄严的气派。
我们的社会泛政治化、泛经济化,是造成美感失落的原因,创造力衰颓、想象力窒塞、欣赏力空洞、生活力贫血,现在可能还看不出台北的将来,不过,生活在空气浊劣、交通阻塞、人心焦虑的地方,如果连一点回旋的空间都没有,还谈什么将来?现在就很痛苦难过了呀!
不做无益之事,何以遣有涯之生?生命里有许多看来是无意义的、像美感、像游戏、像创造与想象,可是倘若没有这些,我们每天踽踽街头,就更感觉到前景的仿徨与渺茫,好像夜暗时台北闹区的街头,单调、苦闷,没有生气。
我们需要的不是计划,也不是等待,而是实践。就从每天拉开和放下铁卷门时开始吧!是不是愿意给点色彩呢?不一定是名画家,家里在读小学的孩子,不就是最好的画家吗?让他试试。
正这样想,我走过一个社区公园,看见四个庞大、丑怪,被称为“外星宝宝”的垃圾桶,使我忍不住叹息,这是世纪末最难看的产物。如果我们的环境保护和卫生工作都由一群没有美感的人为所欲为,城市文化还有什么明天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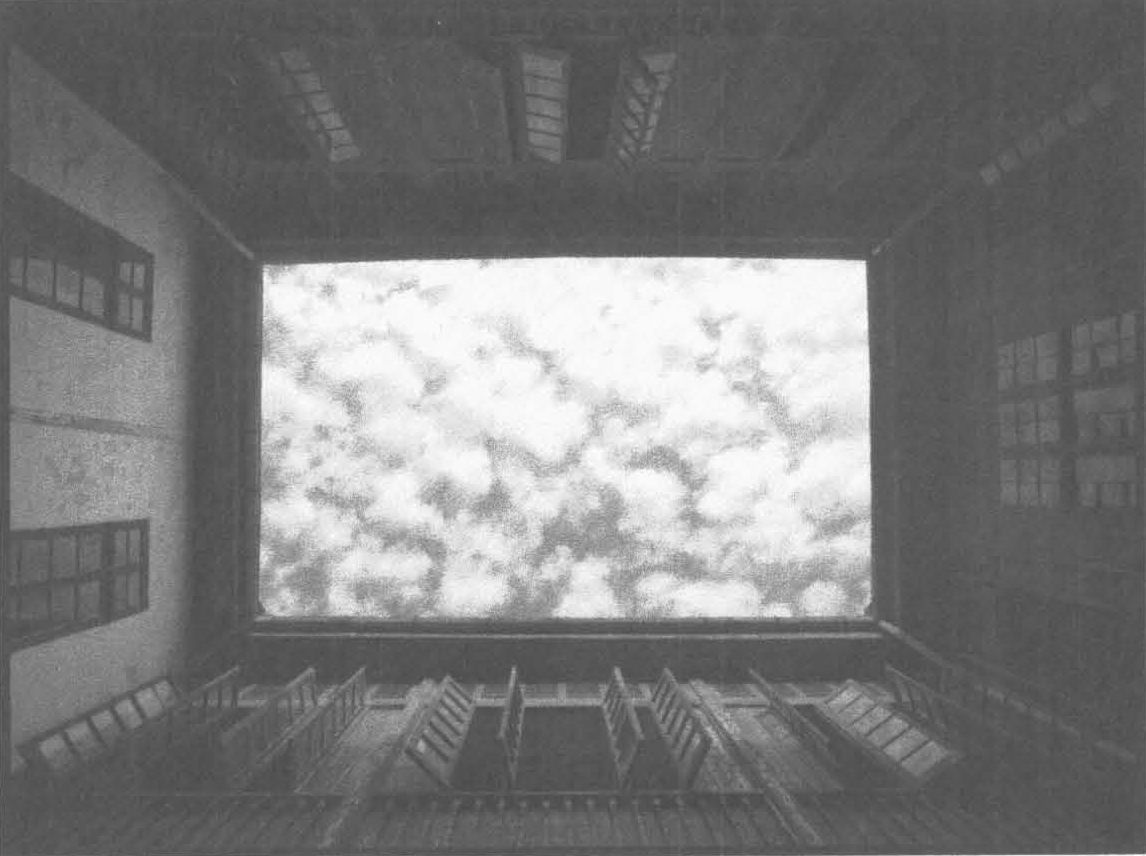
阿火叔与财旺伯仔
随着岁月,我愈来愈能了解父亲少年时代的梦。其实,每个人都有过山林的梦想,只是很少很少有人能去实践它。
十年没有上父亲的林场了,趁年假和妈妈、兄弟,带着孩子们上山。
车过六龟乡的新威农场,发现沿途的景观与从前不大相同了,道路宽敞,车子呼啸而过。想到从前有一次和哥哥坐在新威学校门口,看一小时才一班的客运车,喘着气登山而去,我对哥哥说:“长大以后,如果能当客运车司机就好了。”然后我们挽起裤管入山,沿山溪行走,要走一个小时才会到父亲开山时住的山寮。那时用竹草搭成的寮仔里,住着父亲和他的三位至交阿火叔、成叔、财旺伯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