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(第2/6页)
乱世之中的读书种子闻讯如得佳音。只是战火阻隔,道路迢递,要来读书,也不容易。王明于1939年2月4日致函傅斯年:“闻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徙昆明,生以前考取之研究生资格,请求入所研究,可否?敬乞核示。”傅斯年很快回信应允。但王明6月12日再函傅斯年:“生本拟即日离桂,奈何忽患疟疾缠身未痊,俟病愈则俶装入滇。” 2
周法高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上大三时,卢沟桥事件爆发,他随校迁到重庆沙坪坝。大学毕业,报考北大文研所。那时大学四年级通常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。他的论文利用了《经典释文》的部分材料,使用陈澧《切韵考》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,写了一篇《经典释文反切考》。他将论文寄往昆明,取得考试资格,笔试过后,又在重庆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。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,也很放得开。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,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,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。傅斯年对他相当满意,最后对他说:“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,将来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。”几句话就铸定了一个未来的语言学家的模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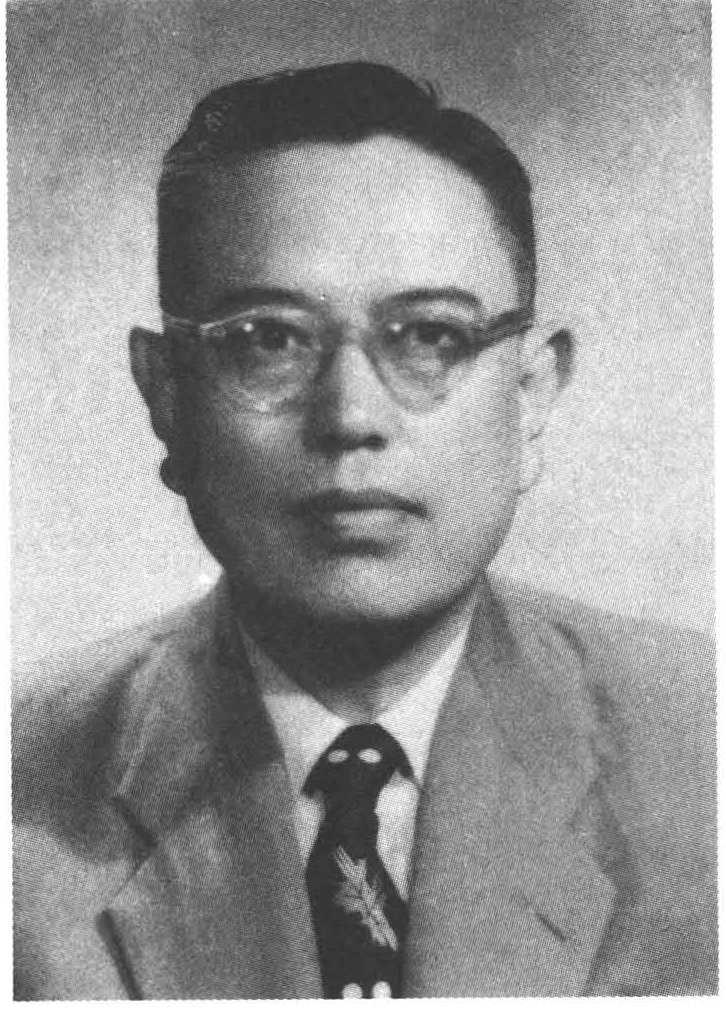
语言学者周法高。
南开历史系学生杨志玖随校南迁,先在云南蒙自县读西南联大分校,1938年暑期毕业后到达昆明。据他回忆:
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(行迈)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。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,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,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,自己看书学习。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、伙食、买书和零用。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,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。这一年,我写了一篇《元代回回初考稿》。1939年秋,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,由先生任所长,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。先生劝我们报考。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,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,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。3
新恢复的文研所首届招收了十名研究生,其中语言组有马学良、周法高、刘念和,文学组有阴法鲁、逯钦立,哲学组有任继愈、王明,史学组有杨志玖、汪籛、阎文儒等。师生们同灶吃饭,彼此关系亲密。文研所傅斯年与郑天挺的姓氏与正副所长音同义乖。治音韵学的周法高编过一副对联:“郑所长,副所长,傅所长,正所长,正副所长;甄宝玉,假宝玉,贾宝玉,真宝玉,真假宝玉。”对仗并不工稳,同学喊起倒也有趣。后来传到周法高的导师罗常培耳中,他把周法高叫来,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,不要逞歪才。任继愈回忆:
研究所刚成立时,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。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。陈先生身体素弱,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。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,难免互相干扰,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,晚上九时以后,他要休息(左右邻居,楼上楼下,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、郑天挺、姚从吾、汤用形诸先生都住在这里),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。有一天,楼下傅斯年、罗常培、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,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,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。傅、罗、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,一时变得“四壁悄然”。4
在敌机的轰炸下,北大文研所很快结束了这段在城里的日子,迁到史语所所在的龙泉镇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。傅斯年既是史语所所长,又兼北大文研所所长,有时两头受累顾此失彼。他在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诉:“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,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,除教授兼导师外,请了向觉明(向达)作专任导师,邓广铭作助教,考了十个学生,皆极用功,有绝佳者,以学生论,前无如此之盛。汤公(汤用彤)公道尽职,指导有方;莘田(罗常培)大卖气力,知无不为,皆极可佩。此外如毅生(郑天挺)、公超(叶公超)、膺中(罗庸)皆热心,只有从吾(姚从吾)胡闹。此人近办青年团,自以为得意。其人外似忠厚,实多忌猜,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,寅恪断为‘愚而诈’,盖知人之言也……我自求代理此事,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,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,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:真不值得。”5对此,傅斯年也有顾虑,几次想推掉北大文研所的事。因昆明再遭轰炸,史语所拟迁四川南溪县李庄。他也就想借坡下驴。9月7日郑天挺致信傅斯年:“此外尚有一事,即北大研究所所址,非随史语所不可,此事已数向兄言之,而兄皆似不甚以为然。但细思之,北大无一本书,联大无一本书,若与史语所分离,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。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,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,盖我曹之高徒,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韧始,岂不大糟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