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卷 波罗蜜(第19/22页)
因此,我特别崇仰那些以自己为流行的人,像摄影家郎静山,九十年来都穿长袍,没穿过别样式的衣服(他今年一百零一岁,据说十岁开始穿长袍);像画家梁丹丰,五十年来都穿旗袍(只偶尔为了方便,穿牛仔裤和衬衫);像《民生报》的发行人王效兰,三十年来都穿旗袍(不管是在盛大的宴会,或球赛现场)。他们不追逐流行,反而成为一种“正字标记”,不论形象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—我甚至不敢想象郎静山穿华伦天奴西服,梁丹丰与王效兰穿圣罗兰、卡迪尔套装时,是什么样子。
所以有信心、有本质的人,流行是奈何不了他的,像王建煊的小平头、吴伯雄的秃头、赵耀东的银头,不都是很好看吗?有的少女一年换几十次头型,一下子米粉头、一下子赫本头、一下子朋克头,如果头脑里没有东西,换再多的头型也不会美的。
流行贵在自主,有所选择,有所决断。我们也可以说:“有文化就有流行,没有文化就没有流行。”对个人来说是如此,社会也是如此。
我们中国有一个寓言:
有一天,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下凡,在路边遇到一个小孩子哭泣不已,他就问小孩子:“你为什么哭呢?”
小孩子就说:“因为家贫,无力奉养母亲。”
“我变个金块,让你拿回去换钱奉养母亲。”吕洞宾被孩子的孝思感动,随手指着路边的大石头,石头立刻变成金块。当他把金块拿给孩子时,竟被拒绝了。
“为什么连金块你都不要呢?”吕洞宾很诧异。
孩子拉着吕洞宾的手指头说:“我要这一只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头。”
这个寓言本来是象征人的贪心不足,如果站在流行的立场来看,小孩子的观点是对的,我们宁可要点石成金的手指,不要金块,因为黄金有时而穷(如流行变幻莫测),金手指则可以源源不绝。
什么是流行的金手指呢?就是对文化的素养、对美学的主见、对自我的信心,以及知道生活品味与生命品质并不建立在流行的依附上。
有一阵子,台湾男士有这样的流行:开奔驰汽车,戴劳力士满天星手表,用都彭打火机,喝XO,穿路易·威登的皮鞋,戴圣罗兰的太阳眼镜,穿皮尔·卡丹的西装,甚至卡文·克莱的内衣裤(现在依然如此流行)。这样人模人样的人,可能当街吐槟榔汁,每开口的第一句是三字经,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通缉犯。想一想,流行如果没有文化、美学、品味做基础,实在是十分可悲的。
讲流行讲得最好的,没有胜过达摩祖师的。有人问他到震旦(中国)做什么?他说:
“来寻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。”
一个人如果有点石成金的手指,知道麦田里的麦子都差不多大,那么,再炫奇的流行也迷惑不了他了。
前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得奖影片《上班女郎》,里面有句精彩的对白:
“我每天都穿着内衣在房间里狂舞,但是到现在我还不是麦当娜。”
是的,我们永远不会变成流行的主角,那么,何不回来做自己的主角呢?当一个人捉住流行的尾巴,自以为是流行的主角时,已经成为跑龙套的角色,因为在流行的大河里,人只是河面上一粒浮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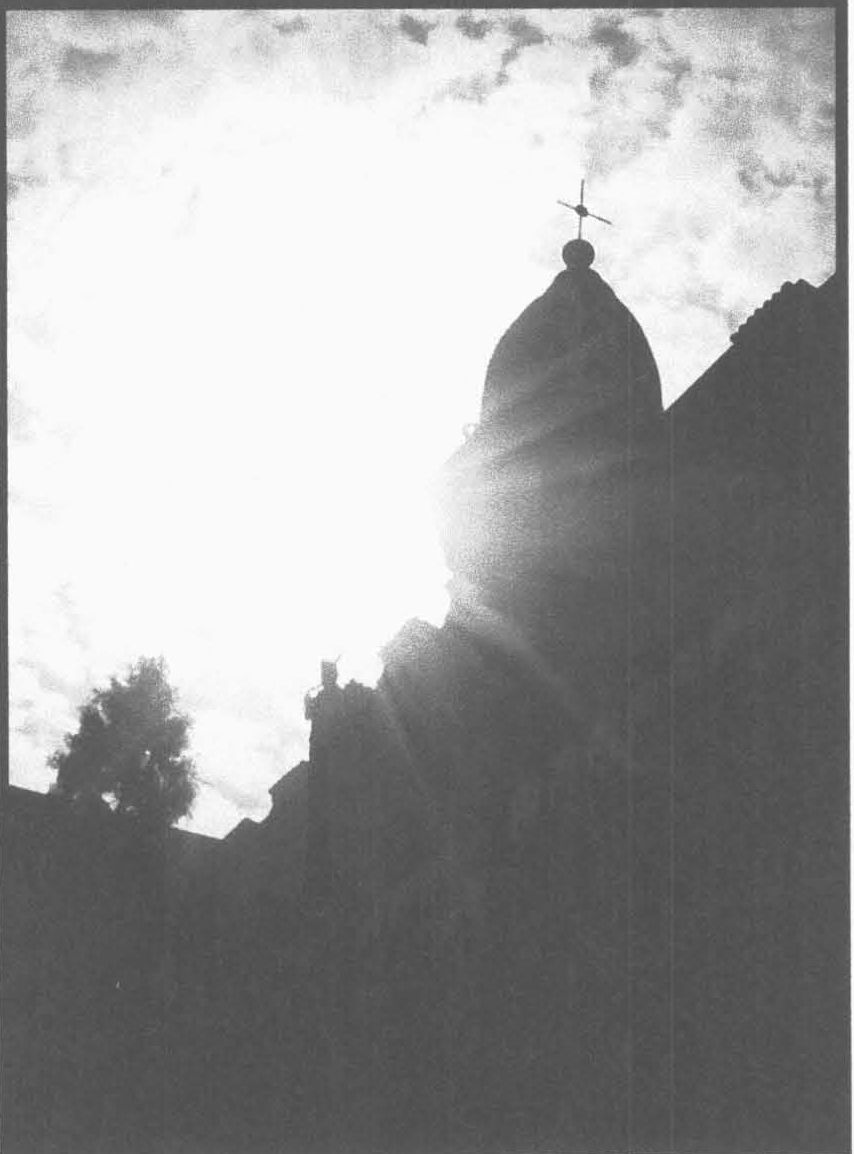
新美学主义
一个新美学主义者充满信心,因为他追求真实有风格的美,他喜欢合理的生活对待,他知道物质之外有美感的真价值,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奈何他呢?何不大家一起来做新美学主义者?
“欧洲皇后”选美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土地举行,却选择了亚洲的台湾。这有一个重大的原因,就是现代女性意识抬头了,使得欧洲人普遍对把女人当花瓶的选美活动失去兴趣。但是在台湾,选美的感冒症候虽已退烧,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选美,欧洲皇后在台湾诞生也就没有什么惊奇的了。
虽说选“欧洲皇后”,大部分参加的都是十七八九岁的小姑娘,她们多数表示对台北这个城市印象深刻。(交通如此混乱、空气如此污浊、物价如此高昂,谁不印象深刻呢?)特别是台北的物价。主办单位曾安排这一群来自欧洲的小姐去逛百货公司,几乎所有的欧洲小姐看到标价都大喊太贵,即使是来自富裕的法国、瑞士、丹麦、德国的小姐都说:“台北的东西贵得不可思议。”东欧几个国家的小姐,就更不必说了。
主办单位为此伤脑筋,听说要特别安排中华商场、西门町、万华等地去购物,以免让她们留下台北物价不合道理的印象。
这个新闻极有参考价值。我虽然住在台北,并未“当局者迷”。和欧洲的小姐一样,我在逛百货公司时,把标价牌拿起来看价钱的那一刻,常常有“是不是贴错了?”的感觉。一件普通平凡的服饰至少都要上千,“并不怎么样”的则要五六千,“看起来还不错”的往往一不小心就是五位数了。有时误以为自己眼花,等清楚数一次是五位数时才叹息地离开。